哥谭市的雨总是带着股铁锈味。布鲁斯·韦恩站在韦恩庄园的墓室前,黑色大衣被风掀起又落下,露出腰间那枚刻着”J”字母的怀表——那是阿尔弗雷德·潘尼沃斯的遗物。墓碑上的照片里,老管家正眯眼笑着,像往常递来热可可时那样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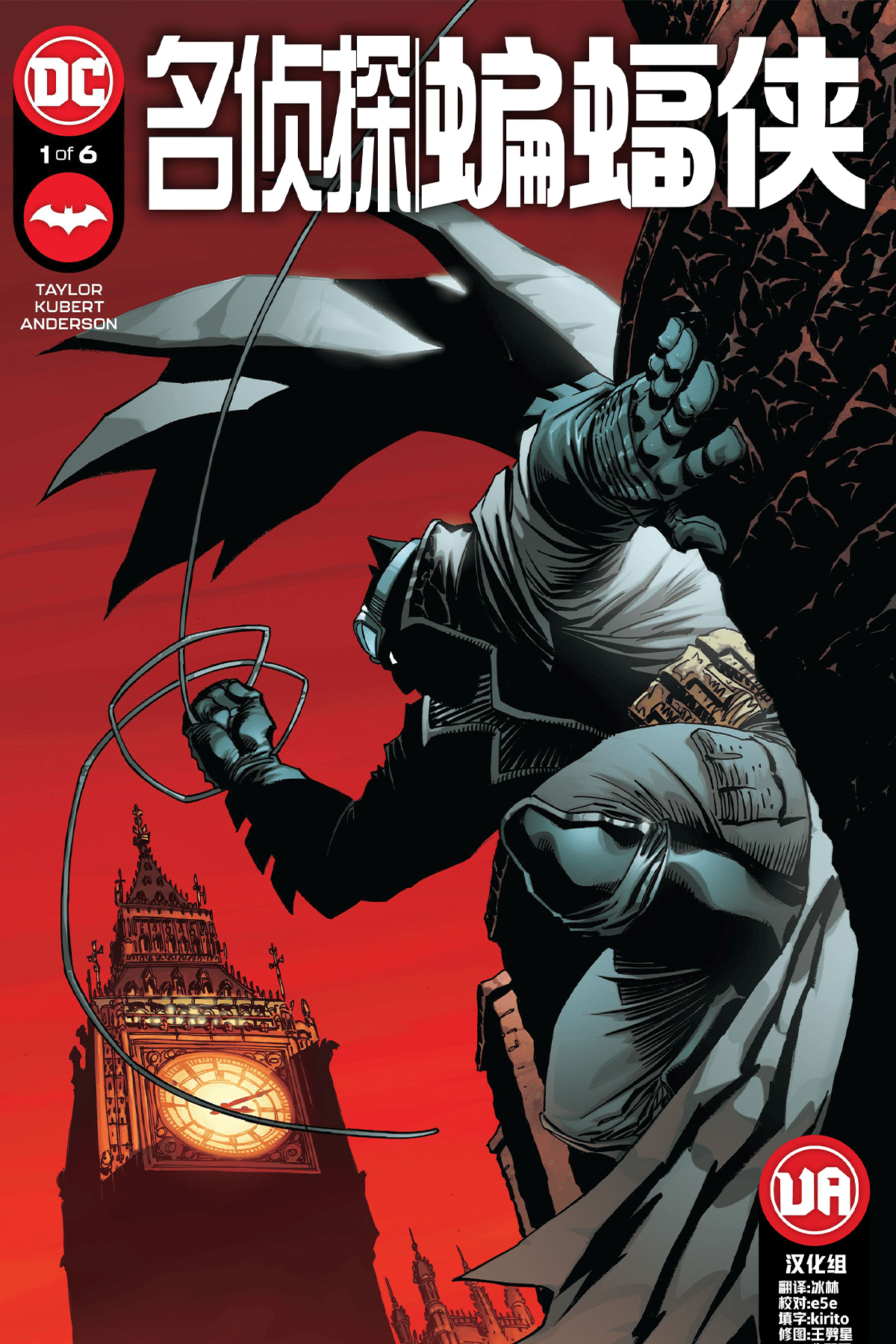
“您说过,要替所有没机会长大的人站岗。”他的指尖抚过冰凉的大理石,声音轻得几乎被雨幕吞没,”可现在…连您都不在了。”
守墓人撑着伞远远站着,不敢打扰这位哥谭市最孤独的守护者。三天前,医院的心电图拉成直线时,布鲁斯正在哥谭港追捕最后一个”儿童走私链”的头目。等他赶到医院,阿福的手已经冷了。老人临终前攥着他的披风,喉间发出模糊的气音:”布鲁斯…别让蝙蝠灯…熄灭…”
但此刻,蝙蝠灯在哥谭警局的穹顶上明明灭灭,照例有警笛声划破夜空。布鲁斯却觉得那光离他太远了。他最后一次抚摸过庄园里每一张老照片,把阿福最爱的锡制茶具收进橡木箱,然后在黎明前登上了前往欧洲的私人飞机。
阿姆斯特丹的运河泛着青灰色的光。布鲁斯裹着深灰色长风衣,站在运河边的旧书店前。橱窗里摆着一本《十七世纪荷兰海盗秘史》,书脊上的烫金字在晨雾中若隐若现。这是他此行的第三个目的地——最近三个月,欧洲多地接连发生离奇案件:巴黎卢浮宫的《蒙娜丽莎》画框被替换成空白画布,罗马斗兽场的地砖下挖出刻着蝙蝠标志的骸骨,布拉格查理大桥的石狮子口中塞着染血的蝙蝠镖。
更诡异的是,所有案发现场都留下了相同的痕迹:一滩未干的白颜料,形状像展开的蝙蝠翅膀。
“您要找的答案,可能在教堂的钟楼里。”书店的白发店主突然开口,目光穿过布鲁斯的墨镜,”三天前有个穿白斗篷的女人来问过这本书,她说…蝙蝠的影子,从来不会只停在一个地方。”
布鲁斯的手指微微收紧。他记得这种语气——像极了当年在哥谭大学帮他整理犯罪心理学的劳拉教授,那个总爱用蝴蝶标本打比方的女人。
巴黎的雨夜来得猝不及防。布鲁斯站在圣心大教堂的穹顶下,雨水顺着彩绘玻璃的缝隙滴落,在他脚边积成小水洼。下方广场上,一群穿白色蝙蝠衣的人正围着喷泉起舞。他们的面甲泛着冷光,斗篷在风中猎猎作响,手中举着的火把将影子投在墙面,竟拼凑出一幅动态的《最后的晚餐》——只不过犹大的位置,站着个穿着黑色披风的轮廓。
“欢迎来到’净化者’的审判日。”扩音器里传来变声后的机械音,”五百年前,蝙蝠侠的血脉在这里埋下罪恶的种子;五百年后,我们要用他的恐惧,洗清每一寸被他’拯救’过的土地。”
布鲁斯的手指按在腰间的电击器上。他能认出那些白色斗篷的材质——和五年前在哥谭码头截获的”死亡天使”团伙用的防弹纤维同源。但更让他心悸的是,人群中飘来的若有若无的古龙水味,那是…阿尔弗雷德常用的”银桦”?
“布鲁斯。”
身后传来熟悉的嗓音。他猛地转身,却在转角处撞进一个温热的怀抱。是露易丝·莱恩,她的红发沾着雨珠,手里举着台微单:”我在拍他们布置现场的样子,这些白斗篷的胸口绣着拉丁文——’Ex Oblivione’,意思是’遗忘’。”
相机屏幕亮起,最新一张照片里,为首的白蝙蝠衣者胸口的刺绣清晰可见。布鲁斯放大图片,瞳孔骤缩——那不是刺绣,是烧灼的痕迹,和他在罗马骸骨旁发现的符号完全一致。
“他们在找什么。”他低声说,”不是艺术品,不是骸骨,是…记忆。”
布拉格的老城区像座迷宫。布鲁斯跟着露易丝钻进一条铺满鹅卵石的小巷,尽头是间挂着”吸血鬼博物馆”招牌的古董店。店主是个戴单片眼镜的老人,看见他们便露出狡黠的笑:”我就知道你们会来。上周有个穿白斗篷的男人来问过,他说要找’被蝙蝠带走的时间’。”
老人掀开柜台下的暗格,取出一本泛黄的日记本。第一页的字迹颤抖着,像是用左手写的:”1643年11月23日,暴雨。我在教堂的忏悔室听见一个声音,他说’我会永远守护这座城市’。但三天后,我的女儿死在巷子里,凶手的靴子上沾着…白色的绒毛。”
后面的页码被撕掉了大半,最后几页夹着张老照片:1920年的哥谭街头,一个穿黑色披风的男人抱着襁褓中的婴儿,背景里是个举着火把的白斗篷女人。照片背面写着:”她说是来讨债的,但我知道,她是来送别的。”
“讨债?”露易丝皱眉,”这和现在的’净化者’有什么关系?”
布鲁斯的手指停在照片角落——婴儿的襁褓上,绣着一只小小的蝙蝠。他的呼吸突然急促起来。那是…他从未见过的家族纹章。记忆如潮水涌来:十二岁那年,他在阁楼翻到过半本烧焦的日记,里面提到”被诅咒的血脉”;十八岁去欧洲游学,在佛罗伦萨的古籍店见过类似的符号…
“他们在清除证据。”他猛地合上日记本,”所有能证明蝙蝠侠家族与欧洲有联系的痕迹。阿福…阿福是不是知道什么?”
露易丝没有回答。她指着窗外——街角的咖啡馆里,一个穿白色斗篷的女人正坐在靠窗位置,面前摆着杯未动的卡布奇诺。她的面甲摘掉了,露出一张苍老的脸,左眼下方有道狰狞的疤痕,像道凝固的泪痕。
“那是…玛莎·韦恩?”露易丝倒吸一口凉气。
布鲁斯的手指深深掐进掌心。他想起母亲临终前的画面:她穿着白纱裙,倒在血泊里,脖颈处的咬痕还渗着血。而眼前的老妇人,分明比母亲年轻至少二十岁。
“跟我来。”他拽着露易丝冲进巷口,却被一声尖锐的刹车声拦住。三辆黑色厢型车从街尾疾驰而来,车门打开,十二名白蝙蝠衣者持枪而立,为首的正是方才在圣心大教堂见过的”审判者”。
“蝙蝠侠先生,”机械音里带着诡异的温柔,”我们等您很久了。您母亲的遗物,该物归原主了。”
地下墓室的空气异常闷湿。布鲁斯被按在石椅上,头顶的水晶灯晃出斑驳的光影。审判者的面甲不知何时摘掉了,露出一张和他有七分相似的脸——同样的高鼻梁,同样的灰眼睛,只是左眼下多了道疤。
“我是塞巴斯蒂安·韦恩,”男人抚摸着石桌上的家族纹章,”您母亲的弟弟,您的舅舅。”
布鲁斯的血液瞬间凝固。他想起阿福临终前欲言又止的模样,想起家族档案里”1912年韦恩家族欧洲分支全员遇难”的记录,想起母亲日记本里反复出现的”西西里的秘密”。
“五十年前,我找到您母亲时,她正抱着您在教堂祈祷。”塞巴斯蒂安的声音里带着怨毒,”她求我放过您,说’蝙蝠侠的使命不该由他承担’。可您知道吗?正是她的软弱,让我们韦恩家的罪孽延续至今!”
他指向墙上的投影——那是哥谭市立图书馆的绝密档案:1888年,韦恩家族资助的”疯人院”发生大火,三百名病人葬身火海;1929年经济危机中,韦恩企业暗中操纵股市,导致欧洲十二家工厂倒闭;2005年,哥谭港的”儿童疫苗运输船”沉没,官方报告称是意外,实则是韦恩集团为了垄断市场…
“您的蝙蝠灯照亮了哥谭的夜,却让我们韦恩家的血债越积越厚!”塞巴斯蒂安抓起桌上的火把,”现在,我要让所有人看清——所谓的黑暗骑士,不过是披着披风的刽子手!”
露易丝的尖叫被枪声打断。布鲁斯望着逐渐逼近的白斗篷们,突然笑了。他想起阿福教他拆解炸弹时的话:”恐惧是弱点,但如果能转化为愤怒…那便是最锋利的武器。”
“你错了,舅舅。”他挣脱束缚,抓起桌上的水晶镇纸砸向投影仪,”蝙蝠侠的使命从来不是守护韦恩家的荣耀,而是守护那些…值得被守护的人。”
阿福的声音突然在他耳边响起:”布鲁斯,真正的侦探,要学会在废墟里找真相。”
他猛地扯下外套,露出里面的黑色战衣。披风在空中划出弧线,像只归巢的蝙蝠。塞巴斯蒂安的火把掉在地上,照亮墙上的另一张照片——1947年,年轻的布鲁斯·韦恩站在罗马斗兽场前,怀里抱着个穿白裙子的小女孩。
“那是我的女儿,”塞巴斯蒂安喃喃道,”您母亲说要送她去美国读书,可火车…火车出轨了…”
布鲁斯的瞳孔微微收缩。他想起母亲日记本最后一页被撕掉的内容,想起自己梦中反复出现的小女孩的笑声。原来那些被”净化者”清除的痕迹,从来不是为了掩盖韦恩家的罪孽——是为了隐藏一个母亲为保护儿子,亲手斩断的血缘羁绊。
“所以你杀了她。”布鲁斯的声音冷得像冰,”因为你无法接受,她选择了蝙蝠侠,而不是你。”
塞巴斯蒂安突然崩溃地跪在地上,白斗篷散落在地,露出里面褪色的红裙——那是小女孩最爱的颜色。他抓着自己的脸,指甲在皮肤上划出血痕:”我只是想让她看看…她的家族有多伟大!可她宁愿跟着你当那个见不得光的蝙蝠…”
黎明前的阳光透过通风口洒进墓室。露易丝举着相机记录现场,警笛声从远处传来。布鲁斯站在塞巴斯蒂安面前,后者已经被戴上手铐。
“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?”他问。
塞巴斯蒂安惨笑:”因为我老了,活够了。但更重要的是…”他看向墙上的照片,”我想让您知道,您母亲从未后悔生下您。她只是…太害怕您变成另一个我。”
走出墓室时,晨雾已经散去。露易丝把相机递给他,屏幕上是刚才抓拍的照片:布鲁斯站在阳光下,披风被风吹起,胸口的蝙蝠标志闪着微光。
“你看起来…不像在逃避了。”她说。
布鲁斯望着远处的圣维特大教堂,轻声说:”阿福说过,侦探的工作不是寻找答案,而是学会和问题共处。现在我知道了——有些伤痕永远在,但它们会成为…让我更强大的理由。”
手机震动起来,是戈登警长的短信:”哥谭港截获一批白色蝙蝠衣,上面有韦恩家族的旧徽章。需要您回来做证物鉴定。”
布鲁斯笑了笑,把手机放回口袋。他转身走向等待的汽车,晨光照亮他的侧脸——那是属于黑暗骑士的坚定,也是属于名侦探的敏锐。在欧罗巴的迷雾中,他终于找到了丢失的答案:蝙蝠侠的使命,从来不是活在过去,而是用过去的伤痕,照亮未来的路。